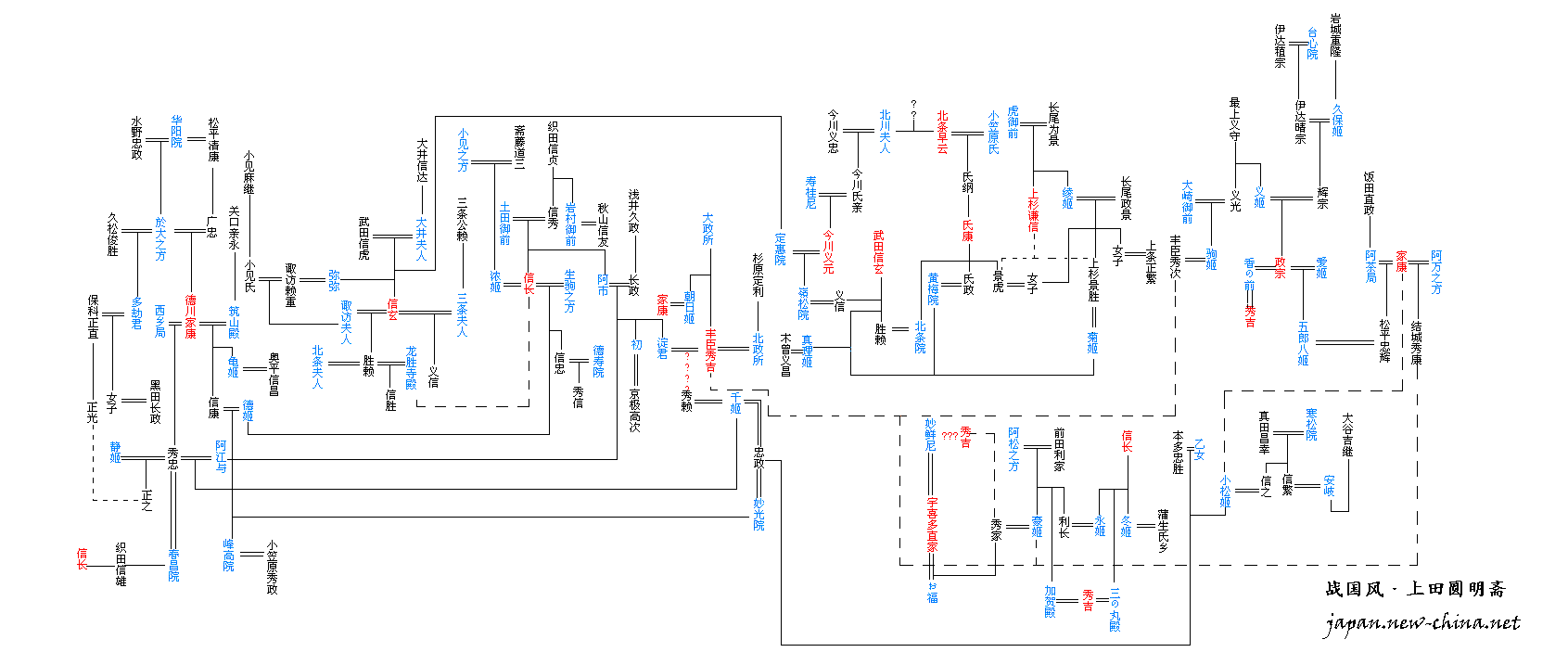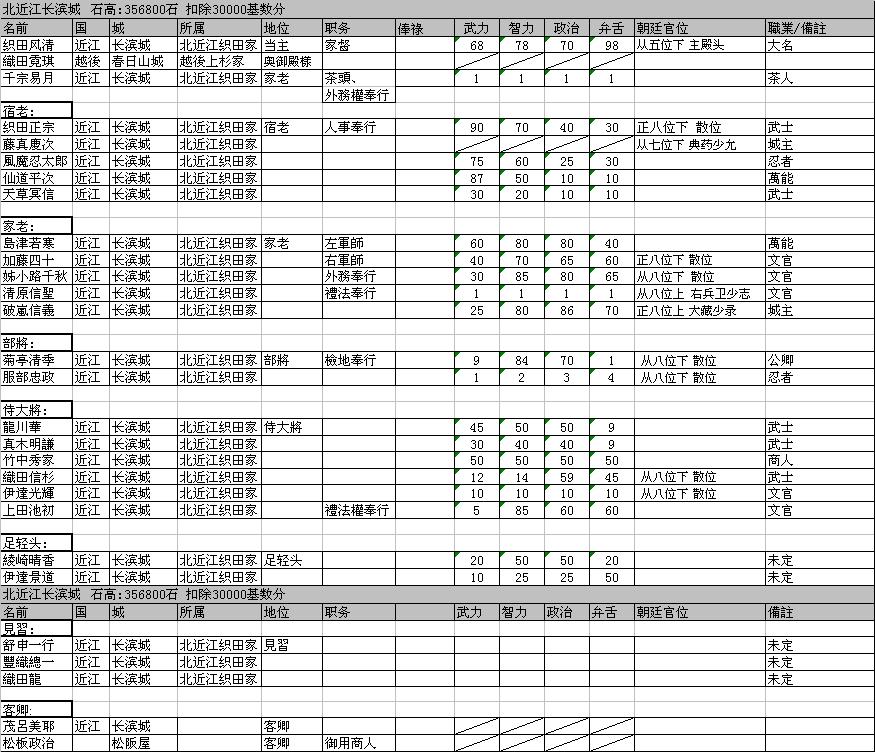(一)血案)
六月的近江,琵琶东岸,渔村外的一条小道上,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人。两个都穿着寻常武士打猎穿的衣服,一个穿的褐色,貌似三十来岁,身材高大厚实,不戴帽,剃了个光头。黑脸、粗眉、丹凤眼、大鼻梁、厚嘴唇,最有特点的就是那看似钢针般要扎人的络腮胡。一双大脚走起路来大步流星。开心地扯着喉咙向后面那位喊:“梅雪!你小子走快一点!蚂蚁都被你踩死一大片啦!再不走快点可没鱼吃啦!”
“呃。是,正宗大人。”后面这位约接近二十岁的样子,身材比那个叫正宗的矮一大截,着白衣服,头戴一顶乌帽子。皮肤析白,长得眉清目秀,不时拿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。
“学人家公卿干嘛?咱们是豪族出身的大名家,可不是那些个搽脂涂粉牙齿漆黑的家伙。堂堂男子汉就得有个男子汉的样子。热了就脱衣服,你看我,袖子也扎起来,裤管也扎起来。不就图个凉快吧嘛。”正宗停下脚步,转过身笑咪咪地看着菊子。
“说什么这边风景不错,还有鱼吃我才跟来的。天不亮就出来了,到现在走了好几个时辰了。又热得要命。早知道就不出来了。”菊子一屁股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面,摘下帽子扇风。
“喂!菊子!你可是坐在地藏菩萨头上的!”正宗叫起来。
“啊?”菊子跳起来,拜倒在地,给地藏菩萨磕头。口里还说着大堆好话。等他说完,抬起头来,却发现没了正宗的踪迹。四下张望却发现正宗伏在悬崖边,于是连忙跑过去,正宗转过头来,示意他低下身子慢慢过去。
“怎么了?大人?”菊子轻声问。
“没闻到血腥味吗?菊子?”正宗故意把鼻子抽了抽然后看看菊子。
“可是您不是说是在渔村附近了吗?会不会是渔夫杀鱼后鱼血的腥味?”
“绝对不可能,鱼血味不是这样的。而且,我看到一艘陌生的船。”正宗拔出刀,说:“你留在这里,我去看看,有什么事我叫你。你注意隐蔽好,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叫我。也不知道权兵卫一家怎么样了。
“大人一定要小心啊。”菊子下意识地往怀里摸东西,却是把扇子。“原来我带着扇子啊。”
权兵卫是以前给正宗抗枪的足轻,跟了他好几年。因为一次战斗中腿部受了伤,没发打仗了,所以回了家继续当渔民。虽然是这样,正宗还是很挂念他的,没月都会给他在时的俸禄。而权兵卫也每隔一阵进城送几尾大鲤鱼给正宗。
慢慢接近村子边。正宗看到了他前所未见的景象,虽然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仗,见过那么多死人和残酷的场景,但是此时却让他感受到了阿鼻地狱般的场景:当他赶到村子临近湖边的空地时,看到了5个水贼打扮的家伙正在活活地割一个渔民的脖子,在渔民的惨叫声中,血顺着脖子流向地上的水罐。而权兵卫正被绑在一旁的柱子上,双脚被砍断了,嘴里流着血,说不出话来,大概是被割掉了舌头。被放完血的那个渔民被扔到了一边-----那里已经堆满了尸体。正宗心里骂道:“畜生啊!”正盘算着怎么去干掉他们,一个戴斗笠的水贼走了过来,正宗闪在一边的屋后。那家伙好象要脱裤子拉屎,正宗闪过去,拉他到屋后,一手把住他的脖子,喀嚓一声就扭断了,那家伙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做了死鬼。
换上了那家伙的衣服,正宗把斗笠压地低低的,径直走了过去。
“快过来帮忙。这家伙力气真大呀。不让他最后死难消气。”一个水贼说道。
他们现在要对权兵卫动手了,正宗拔出刀来。“好,你来。老子都割累了。”正宗看了一眼权兵卫,然后两刀划个十字切,砍下了两个并排按住权兵卫双膝的水贼,劈开了和自己说话的那个家伙。搬尸体那两人回来了,看见此景,举刀冲了过来。正宗将刀向其中一个扔去,插了个透心凉,又对另一个赶上来的发出一声犹如地狱恶鬼般的大吼。那家伙便扑倒在地,七孔流血而死,估计是被震碎了五脏六腑。
正宗抱起权兵卫,一滴眼泪滴在了这个到死都不屈服的老部下脸上。劝兵卫嘴角微微向上翘了翘,脖子向边上一歪,只有出气,没了进气。
从船仓里跑出来好几个水贼,全是被正宗那一声大吼引出来的。当他们看到这个人的如阿修罗般的双眼,听到野兽般的沉重呼吸的时候,全呆住了。
“正宗大人!”菊子跑下来了,鞋子已经跑掉一个,身上几乎被汗水打了个透。
“正、正宗。。。!织田正宗!”其中一个水贼绝望地大叫起来。其他水贼也流露出恐惧的眼神。
正宗慢慢地提着那把滴着血的刀,向他们走去。水贼全扑倒在地上,叫着饶命。正宗走到一个跟前,手一扬。其中一个的身子就被斜着削去了一半。
“饶命啊!正宗大人!我等也是被逼的啊!”剩下的全叫起来了。
“正宗!听听他们说完再杀也不迟啊!”菊子叫起来。正宗没有停手,又砍了一个脑袋。两人的血把剩下的几人染成了红色,仿佛是在血河中浸泡过的恶鬼。“正宗!”看情形这下子不会留什么活口了,菊子冲上去,抱住正宗。正宗下意识地把他摔到地上,踩住他的胸口,刀举起来了。
“正宗!我是菊子!我是菊子!我是菊子!我是菊子。。。。。。”菊子嘶声竭力地吼着。正宗才清醒过来,一把拉起他。“咳。。。。。。。好痛。”菊子揉揉自己的胸口。“你差点把我也杀掉了。最好,问清楚。万一真的有人指示呢?”
“啊!是!小的们是被逼迫的啊!”其中一个胆大的申辩道。
“被逼来屠村的吗!”正宗目光如炬的盯着那人。
“那你们为什么要收集血液!到底有什么目的!”菊子道。
“是,是横山城的斋藤信义大人叫我们干的。”另一个水贼见他的胆大的同伙没有被杀,胆子也大了起来。
“放屁!”正宗一脚踹翻他,又一脚上去,踢了一个后空翻,头着地,扭断脖子死掉了。“污蔑我家的支城主!罪不可摄!给你们机会不要,通通去死吧!”菊子还没来得及阻挡,几刀下去水贼就被杀得只剩下一个了。
“正宗!要是真有幕后主使。你把这个也杀了就不能为权兵卫报仇了!”菊子拦住了正宗。
正宗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。便说:“起来说话!今天老爷不杀你了!”
“可是、大人。我、我、我、我起不来了。。。。。。”那家伙大哭起来。
“起不来?”正宗一把拉起来,却闻到一股臭味,原来那家伙屎尿都被吓出来了。
“这件事非同小可,我们最好回城,等报明了殿下,再做计较。您看如何?”菊子捏着鼻子道。
“畜生!”正宗吼道。“你把全村的人埋了!”
夕阳西下,照在水面上,看起来就像一片血海。一片寂静,只有水浪拍打岸的声音和水鸟的悲鸣在村子周围回荡着。